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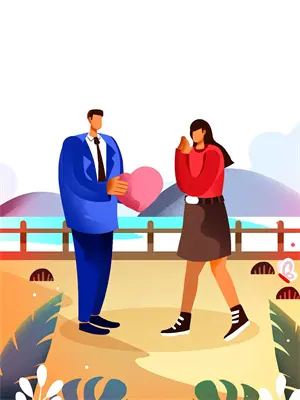
悬疑惊悚连载
由镇魂尺陈薇担任主角的悬疑惊书名:《镇魂尺是什么样子的本文篇幅节奏不喜欢的书友放心精彩内容:第一山雨误入尸栈黔东南的像是憋了整座苗岭的水从午后开始就没歇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挣扎了三个小雨刷器以最快频率左右摆却连前方五米的路面都无法清晰勾沥青路面被雨水泡得发泛着油腻的轮胎每碾过一块积就溅起半米高的泥打在车身上 “噼啪” 作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拍打车“操!” 我猛地砸了一拳方向劣质塑料的触感硌得指骨生喇叭被这一下震得尖啸起声音刺...
主角:镇魂尺,陈薇 更新:2025-11-05 20:02:22
扫描二维码手机上阅读
第一章 深山雨困,误入尸栈黔东南的雨,像是憋了整座苗岭的水汽,从午后开始就没歇过。
越野车在盘山公路上挣扎了三个小时,雨刷器以最快频率左右摆动,
却连前方五米的路面都无法清晰勾勒。沥青路面被雨水泡得发胀,泛着油腻的黑,
轮胎每碾过一块积水,就溅起半米高的泥浆,打在车身上 “噼啪” 作响,
像是有无数只手在拍打车窗。“操!” 我猛地砸了一拳方向盘,
劣质塑料的触感硌得指骨生疼。喇叭被这一下震得尖啸起来,声音刺破雨幕,
在空谷里撞出几声沉闷的回音,惊得远处竹林里的灰雀扑棱棱飞起,
翅膀上的雨水洒在挡风玻璃上,留下一道道狼狈的水痕,很快又被新的雨帘覆盖。
副驾驶上的陈薇被这声喇叭吓了一跳,原本攥着安全带的手骤然收紧,指关节泛出青白色,
连手背上淡青色的血管都清晰可见。她侧过头看我,脸色比窗外的雨雾还要苍白,
嘴唇抿成一条紧绷的线,声音带着明显的哭腔,像被雨水泡软的棉线:“李哲,怎么办啊?
导航早就没信号了,手机也打不通…… 我们会不会困在这里?”我烦躁地抹了把脸,
掌心瞬间沾满雨水和冷汗。车窗缝隙里渗进来的冷风裹着潮湿的水汽,贴在皮肤上,
凉得人打哆嗦。我掏出手机按亮屏幕,左上角 “无服务” 三个灰色的字像道魔咒,
死死地钉在那里。屏幕背景是我和爷爷的合照,照片里爷爷穿着藏青色的对襟衫,
手里握着一把乌木尺子,笑容慈祥 —— 要是爷爷还在,肯定不会让我接这种荒唐的活。
三天前,我在古董市场的店铺里接到那封加密邮件时,就该意识到不对劲。
发件人备注是 “匿名客户”,邮件内容简短却古怪:“收购湘西民俗器物若干,
佣金为市场价三倍。核心要求:需亲眼见证一次真正的赶尸现场,需带助理陈薇同行,
她熟悉湘西民俗,可协助记录。”当时我盯着屏幕里的文字,手指在键盘上悬了半天。
三倍佣金确实诱人,我那间小古董店上个月刚亏了房租,正急需一笔钱周转。
可 “赶尸现场” 这四个字,总让我想起爷爷生前的叮嘱:“湘西的‘走尸’‘赶尸’,
都是活人跟死人打交道的营生,沾不得,更看不得 —— 你要是凑上去看,
说不定就被‘缠’上了。”爷爷是湘西李氏的最后一代 “守墓人”,
专司苗岭一带的殡葬礼仪,年轻时还跟过赶尸队,见过不少常人无法理解的事。
他临终前把那把乌木尺子交给我,说那是 “镇魂尺”,能镇住邪祟,
还反复强调:“以后别碰湘西的民俗器物,尤其是跟赶尸、养尸沾边的,会惹祸上身。
”可我最终还是没抵挡住佣金的诱惑,回复邮件确认接单后,
第二天就收到了陈薇的联系方式。她在电话里声音温和,说自己是湘西吉首人,
从小听着赶尸故事长大,还研究过相关民俗,“能帮你分辨赶尸队的真假,
也能记录现场细节”。现在想来,从接下这单活的那一刻起,
我就已经走进了一张精心编织的网。“别慌,先下车看看情况。” 我强装镇定,
拉开车门的瞬间,一股夹杂着冷雨的山风劈头盖脸砸过来,呛得我猛咳了两声。
雨丝像细针一样扎在脸上,疼得发麻。我抬头望了望四周,
浓绿色的楠竹林在雨里晃得人眼晕,竹梢被风吹得弯下腰,
像是在向我们鞠躬;远处的山坳被乳白色的雾霭裹得严严实实,连个像样的轮廓都看不清,
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不知名鸟类的啼叫,在空谷里回荡,显得格外孤寂。这地方太静了。
静得只有雨声、风声,还有自己沉重的心跳声。没有虫鸣,没有蛙叫,
连竹叶摩擦的 “沙沙” 声都像是被雨水吸走了,只剩下一种让人窒息的死寂。
我想起爷爷生前说过的话:“湘西深山里的静,不是真的静,
是有‘东西’在‘听’你 —— 你要是慌了神,它就敢出来缠你;你要是稳住,
它就不敢露面。”陈薇也跟着下了车,她从后备箱里翻出一把折叠伞,
刚撑开就被突如其来的狂风掀翻了伞骨,伞面像朵被揉烂的花。她赶紧把伞收起来,
抱着胳膊躲到我身后,肩膀微微发抖,声音压得很低:“这地方…… 太邪门了。
我奶奶以前说,湘西深山里的‘走尸’,专挑下雨天出来抓迷路的人,会跟着人的脚步声走,
等你发现的时候,已经被缠上了……”“别瞎想,都是老辈人编的故事,用来吓小孩的。
” 我嘴上这么说,心里却发毛。为了这单生意,
我提前在网上查了不少湘西赶尸的资料:说赶尸人多穿黑色长袍,戴宽檐斗笠,
手里摇着一串铜铃,铃声能驱散沿途的野鬼;尸体都戴黑色面罩,穿白色麻衣,
被两根长竹竿从腋下穿过,竹竿两端由赶尸人扛着,
看起来像是尸体自己在走;还说赶尸队只走夜路,遇到活人要绕着走,要是被人撞见,
就得用符纸贴住尸体的额头,防止 “尸变”。这些原本只当是传说的东西,
现在在这深山雨雾里,却莫名地让人信了几分。尤其是脚下的路,越往深处走,越觉得阴冷,
连呼吸都带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像是走进了一座地下墓穴。我眯着眼睛,
借着昏暗的天光往四周扫了一圈,突然,
视线停在了西北方向的山坳里 —— 那里有几点微弱的橙黄色光晕,
像漂浮在黑暗里的鬼火,忽明忽暗,在雨幕中若隐若现。“那边有灯火!
” 我指着那个方向,心里涌起一丝微弱的希望。不管是苗寨的人家,还是山间的客栈,
总比在这荒山野岭里淋一夜雨强。陈薇顺着我指的方向看了半天,才勉强看到那几点光,
她犹豫地咬了咬下唇,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衣袖的边角:“这荒山野岭的,怎么会有灯火?
会不会是……‘鬼火’?我奶奶说,湘西的‘鬼火’是死人的骨头变的,会跟着人走,
引着人往深山里去……”“别自己吓自己,哪来那么多鬼火。” 我打断她,
从后备箱里拖出两个行李箱 —— 一个是我的,
装着换洗衣物和收购器物用的放大镜、软尺;另一个是陈薇的,
她说里面装着 “记录用的笔记本、相机和民俗资料”。箱子在泥地里拖得格外费劲,
每走一步,轮子都会陷进半指深的泥里,留下一串沉重的脚印,
很快又被雨水冲刷得模糊不清。我们沿着盘山公路的护栏往下走,没走多久,
原本就狭窄的路面突然断了,只剩下一条被杂草掩盖的羊肠小道,蜿蜒着钻进楠竹林深处。
竹林里的竹子长得又高又密,碗口粗的竹身挤在一起,枝叶交错着遮住了天空,
连雨丝都只能从缝隙里漏下来,在地面上织出斑驳的光影。竹叶被风吹得 “哗哗” 作响,
像是无数人在耳边低声私语,偶尔有竹枝被风吹断,“咔嚓” 一声落在地上,
惊得陈薇频频回头。她紧紧跟在我身后,几乎要贴到我的后背,
右手始终攥着衣袖里的什么东西,声音压得极低:“李哲,
我总觉得后面有人跟着我们…… 你听,是不是有脚步声?”我停下脚步侧耳细听,
只有密集的雨声和竹叶的摩擦声。“是风吹竹叶的声音,你太紧张了。” 话虽这么说,
我还是下意识地加快了脚步。手里的行李箱拖在地上,
“咕噜咕噜” 的声音在竹林里格外清晰,
反而更让人心慌 —— 这声音像是在给什么东西 “引路”。走了约莫四十分钟,
前方的竹林突然稀疏起来,一栋老旧的木楼突兀地出现在眼前,像从地里冒出来的一样,
带着一股与世隔绝的沧桑感。这栋楼有三层,黑瓦白墙,
飞檐翘角的设计带着明显的湘西吊脚楼风格,却又比普通吊脚楼多了几分阴森。
墙面斑驳得厉害,不少地方的白灰已经脱落,露出里面发黑的杉木,
木头上还能看到隐约的刻痕,像是某种符咒;屋顶的瓦片缺了好几块,雨水顺着缝隙往下滴,
在地面上积出一个个小水洼,水洼里倒映着木楼的影子,扭曲变形,像一张狰狞的脸。
门前挂着两盏红灯笼,灯笼纸被雨水泡得发皱,颜色暗沉,昏黄的光晕透过纸缝洒出来,
在地面上映出一片模糊的红光,像是凝固的血。灯笼下方的石阶上,摆着两个石狮子,
狮子的眼睛被朱砂涂过,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诡异的红,像是在盯着我们看。
最让人头皮发麻的是门楣上的匾额。匾额是深棕色的紫檀木,边缘已经开裂,
上面刻着两个褪了色的楷书大字,字体遒劲有力,却透着一股挥之不去的阴气 ——尸栈。
“尸栈?” 陈薇的声音瞬间发颤,她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抓着我胳膊的手冰凉,
指腹微微出汗,“这名字…… 是专门给赶尸人住的地方吗?我在《湘西民俗志》里看到过,
说以前湘西有‘死店’,就是供赶尸队歇脚的,店里会专门留一间‘尸房’,用来存放尸体,
还会在门口挂红灯笼,告诉赶尸人‘这里可以落脚’……”我心里也是一凛。
爷爷生前确实跟我提过 “尸栈”。他说,清末民初的时候,湘西赶尸业鼎盛,
从沅陵到辰州的路上,每隔二十里就有一家尸栈,栈主大多是懂 “阴阳术” 的人,
知道怎么跟赶尸人打交道,也知道怎么 “安抚” 尸体。
尸栈的规矩很严:赶尸队只能在夜间入住,尸体要放在专门的房间,
活人不能靠近;入住时要登记 “尸体数量” 和 “归乡目的地”,不能多报,
也不能少报;更重要的是,“入夜后不能出门,不能数尸体的数量,
不能问赶尸人的姓名”—— 这些都是 “犯忌讳” 的事,一旦破了规矩,
就可能引来 “尸变”。可那都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新中国成立后,赶尸业逐渐消失,
尸栈也大多改成了普通客栈,或者废弃在深山里。
现在这深山里突然出现一栋挂着 “尸栈” 匾额的木楼,怎么想都透着诡异。正犹豫间,
木门 “吱呀” 一声开了条缝,一股混杂着檀香和腐土的味道从里面飘出来,
还带着一丝若有若无的腥气,像放久了的生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从门缝里探出来,
老人的皮肤干瘪得像脱水的橘子皮,紧紧贴在颧骨上,眼睛浑浊得像两颗蒙尘的磨砂玻璃球,
几乎看不到瞳孔。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粗布长衫,衣角沾着泥污,
领口处缝着一块黑色的补丁,手里拄着一根竹拐杖,拐杖头磨得光滑发亮,
上面刻着一个模糊的 “安” 字。“住店?” 老人的声音沙哑得像是砂纸摩擦木头,
每一个字都磨得人耳朵疼,他上下打量着我们,
目光在我脖子上挂着的铜铃上停留了一瞬 —— 那是我为了这单生意,
从长沙古董市场花八百块买的道具,铜铃直径约三厘米,表面刻着模糊的符文,
卖家说这是 “赶尸人用的引路铃”,能镇住邪祟。“老伯,
我们车坏在前面的盘山公路上了,想在您这儿借宿一晚,多少钱都行。” 我赶紧上前,
尽量让语气显得诚恳,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脖子上的铜铃,心里盼着这道具能起点作用,
别让老人把我们当成不懂规矩的外人。老人没说话,只是缓缓侧身,
让出一道能容一人通过的门缝。他的动作僵硬而缓慢,像是关节生锈了一样,每动一下,
都能听到衣服摩擦的 “窸窣” 声。“进来吧。” 他终于开口,声音没有起伏,
像是在念一段早已背熟的咒语,“记住两条规矩:一,入夜后别出门;二,
不管听到什么动静,都别应声。”我和陈薇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犹豫。
陈薇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袖,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 “我们还是走吧”,可雨还在下,
四周除了这栋尸栈,再也没有别的建筑。我咬了咬牙,拎起行李箱,跟着老人走进了尸栈。
第二章 客栈诡事,赶尸疑云跨过门槛的瞬间,一股刺骨的阴冷扑面而来,不是温度低,
是那种能渗进骨髓的寒意,像有无数只冰冷的手在抚摸你的骨头,让人忍不住打哆嗦。
堂屋里没有通电,只点着一盏油灯,昏黄的火苗在风里微微晃动,把墙上的影子拉得老长,
一会儿像伸着爪子的鬼,一会儿像弯腰行走的人,看得人头皮发麻。地面是青石板铺就的,
石板缝隙里长着暗绿色的青苔,踩上去滑溜溜的,一不小心就会摔倒。墙角堆着几捆干柴,
上面落满了灰尘,柴捆旁边放着一个半人高的黑色陶罐,罐口用红布封着,
红布上还系着一根麻绳,绳子上挂着三枚铜钱,铜钱边缘已经氧化发黑,风吹过的时候,
铜钱会发出 “叮叮” 的轻响,声音脆得像冰,在寂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老人拄着拐杖,
一步一步地往柜台走,竹拐杖敲在青石板上,发出 “笃笃” 的声响,
每一声都像是敲在心上,让人莫名的心慌。柜台是用深色的梓木做的,表面被磨得光滑发亮,
能隐约映出人影,上面摆着一个缺了角的算盘、一个墨水瓶,还有一本摊开的泛黄册子。
“登记。” 老人从柜台下拿出一支毛笔,笔杆上缠着一圈发黑的红绳,笔尖有些分叉,
沾着干涸的墨汁。他把毛笔和一张裁好的宣纸推到我面前,动作缓慢而机械,“姓名,籍贯,
去向。”我愣了一下,手里的行李箱差点脱手:“住店还要登记这些?”“规矩。
” 老人眼皮都不抬,手指了指墙上挂着的另一本册子。那本册子比桌上的更旧,
封面是暗红色的,已经看不出原本的颜色,纸页都卷了边,用一根麻绳系着,
封面中央写着 “客录” 两个字,字迹是用朱砂写的,已经有些褪色,“活人有活人的路,
死人有死人的道,记清楚了,免得走错路。”陈薇在我身后轻轻拉了拉我的衣角,
我回头看她,她脸色苍白,摇了摇头,眼神里带着一丝恳求,像是在让我别多问。我没多想,
拿起毛笔,在宣纸上写下 “李哲,长沙岳麓区,收购民俗器物”,又把笔递给陈薇。
她犹豫了一下,接过毛笔,指尖在笔杆上顿了顿,才写下 “陈薇,湘西吉首市,
协助记录民俗”。老人接过宣纸,看了一眼,又翻了翻桌上的册子。
我趁机瞥了一眼册子里的内容 —— 上面记着不少名字,
大多是 “张三”“李四”“王五” 这种普通得诡异的名字,籍贯都是湘西的老地名,
比如辰州、沅陵、永顺、泸溪,最新一页的墨迹还很新鲜,像是刚写上去没多久:・张三,
辰州,泸溪・李四,沅陵,凤凰・王五,永顺,保靖・赵六,辰州,麻阳这些名字太刻意了,
像是有人故意编造的代号,而不是真实的姓名。我心里泛起一丝疑惑,刚想开口询问,
老人已经把宣纸夹进册子里,动作麻利得不像一个年迈的人。“跟我来,楼上有房间。
” 老人拿起墙角的油灯,转身往楼梯口走。油灯的火苗在他手里很稳,没有晃动,
仿佛不受风的影响。我们跟着老人往楼上走,木楼梯年久失修,
每走一步都发出 “吱呀” 的怪响,仿佛随时会坍塌。楼梯扶手是用竹子做的,
上面包着一层厚厚的包浆,摸上去冰凉光滑,像是摸在人的骨头上。二楼的走廊又深又长,
光线昏暗,只有每隔五米挂着的一盏小油灯,火苗微弱得随时会熄灭,
在墙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走廊两侧的房门都紧闭着,门楣上都贴着一张黄色的符纸,
符纸上用朱砂画着复杂的符咒,符咒的纹路扭曲缠绕,像是在纸上爬动的蛇。
有些符纸的边角已经卷曲发黑,露出里面的木门,木门上刻着细小的 “镇” 字,
一个挨着一个,密密麻麻,像是在反复强调某种禁忌。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还夹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檀香,两种味道混合在一起,让人头晕目眩。“这间。
” 老人在走廊最靠里的一扇房门前停下,用拐杖敲了敲门板,“里面有床有桌,
马桶在床底下,夜壶在桌角。记住我刚才说的规矩,入夜后别出门,
尤其别靠近西厢房 —— 今晚有‘客’来。” 他特意加重了 “客” 字,
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微光,像是在提醒,又像是在警告。“西厢房住的是…… 赶尸人?
” 陈薇忍不住问,声音压得很低,手指紧紧攥着衣角。老人没回答,只是转身往楼下走,
拐杖敲击地板的 “笃笃” 声渐渐远去,留下我和陈薇站在房门口,面面相觑。我推开门,
房间里的陈设简单得过分:一张硬板床,铺着洗得发白的粗布床单,上面有几处深色的污渍,
不知道是霉斑还是别的什么;一张缺了腿的方桌,用一块石头垫着才勉强放平,
桌上放着一个缺了口的茶壶和两个粗瓷碗;墙角立着一个掉漆的木柜,
柜门上挂着一把生锈的铜锁;墙上挂着一面铜镜,镜面模糊得像蒙了一层雾,
照出来的人影扭曲变形,连五官都看不清,反而像是一个模糊的黑影在镜中晃动。
陈薇走进房间,放下行李箱,脸色还是不好看。她走到窗边,推开一条缝往外看,雨还在下,
远处的竹林在雾里晃得人眼晕,只有尸栈门前的红灯笼,在雨幕中泛着微弱的红光。“李哲,
这地方太怪了。” 她转过身,眉头紧紧皱着,“那个老伯的话,
还有那些符纸…… 我们明天一早不管车能不能修好,都赶紧走吧?我总觉得待在这里,
心里不踏实。”我点点头,走到桌前坐下,刚想拿起茶壶倒杯水,却发现壶里是空的。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一阵铃声,断断续续的,像被雨水泡软的铜丝,
却带着一种固定的节奏,一下一下地敲在心上。叮铃…… 叮铃……一长两短,一长两短。
我猛地站起来,走到窗边。这铃声的节奏,
和我之前在资料里看到的 “赶尸铃节奏” 一模一样!资料里说,
赶尸人摇铃有固定的规律,“一长两短” 是在提醒沿途的活人 “回避”,
也是在指引尸体 “跟紧”,防止尸体走失或 “尸变”。“你听到了吗?” 我压低声音,
手指着远处的方向,“是赶尸铃!”陈薇赶紧凑到窗边,侧耳听了一会儿,脸色变得更白了。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笔记本,翻开其中一页,上面画着一个简易的铃铛图案,
旁边标注着 “赶尸铃:一长两短,指引尸群,警示活人”。“真的是……” 她抬起头,
眼神里带着紧张,却又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我们真的遇到赶尸队了!
这可是难得的民俗记录机会……”我愣了一下,陈薇的反应有些奇怪。
正常人遇到这种诡异的场景,应该是害怕才对,可她却提到了 “民俗记录”,
像是早就盼着这一幕发生。但我没多想,只当是她研究民俗太久,一时忘了害怕。
我从行李箱里翻出相机,调好焦距,轻轻推开窗户,冷风裹着一股腥气灌进来,
呛得我咳嗽了两声。远处的山路上,一支诡异的队伍正缓缓走来,在雨幕中若隐若现。
为首的是个披着黑色斗篷的人,斗篷的帽子压得很低,遮住了大半张脸,
只能看到一点苍白的下巴和紧抿的嘴唇。他手里握着一串铜铃,
正按照 “一长两短” 的节奏摇晃着,铃铛上的符文在油灯的微光下闪着淡淡的红光,
像是有生命一样。在他身后,跟着五个高高瘦瘦的 “人”。他们都戴着宽檐的斗笠,
斗笠边缘垂着黑色的布帘,把脸遮得严严实实,看不见表情;身上穿着白色的麻衣,
衣摆拖在地上,沾满了泥污,有些地方已经破烂,
露出里面发黑的布料;胳膊都直直地伸在前面,被一根长长的竹竿从袖子里穿了过去,
竹竿两端由两个穿着同样黑袍的人扛着,看起来像是尸体自己在走。
他们走路的姿势格外僵硬,膝盖直挺挺的,每一步都刚好踏在铃声响起的瞬间,
整齐得不像活人。队伍走得很慢,像是在配合铃声的节奏,每走三步,
为首的赶尸人就会停下来摇一下铃,像是在确认尸体有没有跟紧,又像是在驱散沿途的邪祟。
“一、二、三、四、五……” 陈薇轻声数着,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记录着,
“五个‘尸体’,三个赶尸人…… 符合湘西赶尸队的常见配置。”我举着相机,
放大焦距仔细观察,突然发现不对劲 —— 竹竿穿过的衣袖,明明只有五个,
可在队伍的最后面,还跟着一个 “人”!这个 “人” 也戴着斗笠、穿着麻衣,
却没有被竹竿串着,独自跟在队伍后面,走路的姿势虽然也僵硬,却比前面五个灵活一些,
尤其是膝盖,偶尔会微微弯曲,像是在适应泥地的坡度。更诡异的是,
这个 “人” 的麻衣下摆沾着的泥污是新的,
甚至能看到衣摆下露出的黑色鞋子 —— 那鞋子看起来很新,鞋面上还能看到反光,
根本不像死人穿的寿鞋!而且,它的肩膀微微耸着,像是在刻意模仿前面尸体的姿势,
却又做得不够自然,露出了破绽。“不对……” 我皱起眉头,把相机递给陈薇,“你看,
竹竿穿过的只有五个,可队伍里有六个‘人’!”陈薇接过相机,放大焦距看了半天,
脸色瞬间变得惨白,手里的笔记本 “啪嗒” 一声掉在地上。她指着屏幕里的画面,
声音发颤:“这…… 这多出来的一个……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捡起笔记本,
翻到刚才那一页,发现陈薇在 “五个尸体” 后面画了一个问号,
旁边还写着 “注意:最后一具动作异常”。看来她早就发现了不对劲,只是没说出来。
“不知道。” 我摇摇头,心里涌起一股寒意,“资料里说,赶尸队的尸体数量必须固定,
‘多一具少一具,都容易招野鬼’。这多出来的一具,要么是野鬼附了身,
要么…… 根本不是尸体。”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了敲门声,三长两短,节奏规整,
像是某种暗号。紧接着,是老人沙哑的声音:“几位是辰州张氏的传人吧?里面请。
”我们赶紧关上窗户,屏住呼吸,听着楼下的动静。赶尸人的脚步声很轻,几乎听不到,
只有铃铛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像是走进了西厢房的方向。
“他们住进西厢房了。” 陈薇靠在墙上,脸色苍白,“那个老伯肯定早就知道他们要来,
还特意留了房间…… 这尸栈,根本就是为赶尸队准备的。”我走到铜镜前,
看着镜中扭曲的人影,突然觉得这面镜子有些不对劲。镜面虽然模糊,但仔细看,
能看到镜中映出的房间角落,似乎有一个黑影在晃动,可现实中那个角落空无一人。
网友评论
小编推荐
最新小说
最新资讯
最新评论